
王春成
因涉及某腐敗要案而被調查的遼寧春成工貿集團(下稱春成集團)董事長王春成,在內蒙古還面臨一場礦權歸屬的可能的訟爭。
原籍遼寧省阜新市的民營企業家王春成以修建巴新鐵路聞名,躍進煤礦與阜新新邱露天煤礦堪稱支持其產業擴張的兩大現金奶牛。但由於十年后仍未辦理採礦權變更手續,王春成於2004年初接手的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西烏旗躍進煤礦的採礦權,正遭遇該礦原國企職工的法律追索。
2004年2月,西烏旗政府與春成集團簽署《關於合作開發礦產資源的協議》(下稱合作開發協議),將已進入破產程序的國有躍進煤礦採礦權、礦區土地無償轉讓或劃撥給春成集團。
結合產量與煤價,諸多原國企職工估算,易主后的躍進煤礦為春成集團貢獻的產值在20億元以上,但后者採礦所用的採礦權,至今仍在國有躍進煤礦名下。
換言之,在2004年至今的整整十年內,春成集團一直在無償使用國有的採礦權証從事煤礦開採,並獲得巨大的收益。據此,這些職工希望以訴訟方式收回礦權。
作為當年地方政府國企改制、招商引資大浪潮下的產物,不規范操作的歷史瑕疵遺留至今。
此案經錫盟中級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后,已上訴至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截至《財經》發稿時,后者尚未決定是否受理。
信訪轉司法
職工提起訴訟的初始動機,在於解決企業破產后的補償問題。
躍進煤礦自1958年開始生產,至2003年共有400多名職工,其中正式職工126人,其余為照顧就業的職工子女、合同制工、長臨工等。據職工反映,2003年破產改制時,對於所有職工都隻發了拖欠的工資、補繳了欠繳的社保,但並未給予相應的補償。
時任副礦長李永發介紹,2004年起,職工們就開始赴西烏旗、錫盟和北京上訪,分批次的上訪生涯持續了十年。2012年,西烏旗政府曾下發一個類似總體解決方案的文件,但問題仍未解決。
新一輪的“鬧訪”從2014年2月開始,職工們向旗政府反映問題,后者認為已經出具了答復,雙方陷入僵持。激動的職工們曾在2月和3月,兩次沖進旗政府辦公樓表達訴求,每次都有200人以上。李永發介紹,“旗領導連夜給我們開會,‘你們有事說事,不能這麼鬧’。”
今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依法處理涉法、涉訴信訪問題的意見》,要求“建立涉法涉訴信訪事項導入司法程序機制”。西烏旗現任常務副旗長常勝介紹,“在中央精神的大背景下,我們建議職工們走法律程序。”
“既然政府支持走法律程序,我們沒理由再上訪。”李永發通過網絡檢索,在北京找到企業破產改制領域的律師,旗政府甚至主動提出承擔律師費。
為弄清補償方案,接受職工委托代理該案的北京中咨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韓傳華,查閱了大量早年的改制文件。在查閱躍進煤礦現在的採礦權申請登記書時,他發現,登記書上的採礦權申請人仍為國有企業西烏旗躍進煤礦,隻不過法定代表人換成了王春成--王春成控制的個人公司,一直以申請延續的方式使用原來的國有採礦權証,其最新的延續申請是在2013年。
在進一步的調查中,職工們認為發現了更多的疑點。“這涉及巨大的國有資產流失。”李永發認為,這個發現也增加了職工們的訴求,除了破產補償,他們還希望拿回價值10億元級別的礦權。
改制復盤
與當時其他地方政府一樣,2003年,位於錫林郭勒草原上的西烏旗,也在著手進行兩件事:國企改制、招商引資。
“當時有個改革的大背景,國家讓扭虧無望的國有資產有序退出。”時任西烏旗經貿局局長張世緒回憶,“旗裡的其他地方國企,如乳品廠、皮毛廠、酒廠都已經退了。因為資產重、包袱多,剩下三個地方國營的小煤礦沒退。”西烏旗先將其中最大的白音華一號礦賣給國電平庄煤業,對方答應接收全部職工﹔哈達圖煤礦則實施全員持股改制﹔待改制的隻剩躍進煤礦。
對於改革的必要性,職工們也不否認。在2003年6月14日的工作日志上,時任副礦長李永發在羅列了躍進煤礦的負債后寫道,“改革勢在必行。”當天的班子會議決定,起草方案並向作為主管部門的旗經貿局上報,會上提到了集體參股。
據李永發的工作日志,同年6月23日,班子會議討論了破產以后(改制)資金從哪裡出的問題。最后初步議定,結合200余萬元的企業負債,將企業股本定為260萬元,每股定為2萬元,實行員工出資持股,願意參股的員工最少購買1股,最多購買64股。他們決定查清賬目,讓職工在參股時心裡有底。
6月27日,躍進煤礦全體職工入股改制的動員大會召開,時任副旗長楊立宇、旗經貿局局長張世緒與會。據職工們事后回憶,這是第一次動員大會,會議效果不佳。因為職工們認為每股2萬元定得過高,認購股份並不踴躍。
此后,在第二次動員大會上,與會的班子成員加職工代表有四五十人。張世緒在會上提出,不妨增加股份數量,同時把每股價格縮小,變成一兩千元,以提高大家入股的積極性。會上進行了投票,在職工們的印象中,大家散會后交流,有80%以上的職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不過,改制之事再無下文,直至春成集團接手躍進煤礦。
對於個中原因,雙方各執一詞。多位參與改制的政府領導向《財經》記者回憶,之所以讓春成集團接手,確系兩次動員大會后,職工們並無出資參股意願。另外,企業領導班子不團結,讓班子成員合伙接手的設想也落空了。
職工們則認為,第二次動員大會上多數職工代表都投票同意,但不知為何該投票結果未被採納。並且,在旗政府與春成集團展開接觸時,仍有職工代表找到相關領導要求搞職工持股,但遭到拒絕。
2004年1月,隨著躍進煤礦正式破產,職工們離崗。后來煤礦擴採,存在了46年的企業家屬區也被拆除,原有職工和家屬近千人各自流散並在日后為安置補償持續上訪。
作為當年煤礦主管部門領導,張世緒介紹,他制定過一份躍進煤礦遺留問題的解決方案。他先向躍進煤礦職工征求意見,將問題匯總后起草方案,再將草案拿到旗黨政聯席會議討論以后正式實施。其中關於正式職工的補償,擬定的標准是,基數3000元,外加300元乘以工齡,工作20年的正式職工可以拿到9000元。非正式職工不能拿基數。
在張世緒的印象裡,當時春成集團分幾次共給了數百萬元,“特意打到法院清算組的賬戶上,這樣就能優先保障職工。當時有六聯單,包括煤礦、經貿局、勞動局、就業局、財政局和公証處六方,補償款發放與否一定會有簽字,經貿局會存檔。”
礦權誰屬
至於破產之后的煤礦開發,西烏旗政府(甲方)與春成集團(乙方)於2004年2月簽訂的合作開發協議商定,以現有煤礦為中心,周邊5公裡范圍由乙方勘探並開採,甲方協助乙方辦理勘探開採手續。乙方在一年內投資5000萬元改造現有煤礦,並在日后上馬洗煤廠、自備電站、煤化工等后續產業。
本著吸引投資的原則,西烏旗政府給予了乙方大量優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現有煤礦的開採權歸乙方,甲方將採礦証等証件移交給乙方作為“臨時開採使用”,並負責辦理各種証件的更名事宜。
憑借合作開採協議,春成集團停止了躍進煤礦延續46年的井工開採,投入巨資改造為更為高效和安全的露天開採。據舊有的採礦權証,礦區面積近1.8294平方公裡,生產規模僅每年30萬噸,但依據協議,春成集團將採礦區域擴至5平方公裡,生產規模僅接手第一年即達到150萬噸。
職工們估算,躍進煤礦十年來的產值逾20億元。
合作開採協議中關於採礦權的臨時性安排,卻成為了日后礦權歸屬的焦點所在。躍進煤礦原礦長楊顯斌,在改制后調任西烏旗國土局礦管股股長。楊顯斌回憶幾年后他發現,春成集團在改制后仍沿用原躍進煤礦的採礦証,曾催促對方把採礦權變更至自己名下,“但他們拿出與旗政府簽的協議,說這事歸旗政府辦理,不是企業的責任”。
在楊顯斌調離后,接手的王春成成為躍進煤礦的法定代表人,但由於“辦理各種証件的更名事宜”的協議條款一直未實際履行,使得春成集團在繳納84.32萬元資源價款后,一直沿用舊有的採礦權証至今。
這導致從權利登記人的角度來說,煤礦的採礦權仍屬於至今未注銷法人機構--國有躍進煤礦。
“當年的旗政府在簽協議時,作了一個超越權力范圍的承諾,而且事后也沒有履行。”一位熟悉改制過程的人士在分析此次礦權紛爭的根源時說,“採礦權的變更轉讓,權力在內蒙古自治區國土廳,旗政府怎麼會有權辦理?”
這位人士也談到應歷史地看待這些程序瑕疵,“那個年代,基層政府對相關法律法規並不熟悉,操作時難免不規范。”
發現這一漏洞后,75名職工以這份合作開發協議損害國家、企業和職工利益為由,將春成集團與西烏旗政府及相關部門列為被告,試圖借此收回採礦權,並要求春成集團返還採礦收益以及賠償損失。
2014年6月20日,錫盟中級法院裁定,對這一起訴不予受理。理由是,西烏旗政府當年與春成集團簽訂的合作開發協議,是政府國有部門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的行政性調整。根據最高法院《關於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政府主管部門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不服裁決的職工則委托代理律師向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提起上訴,后者正在研究是否受理該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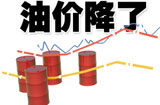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