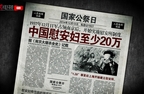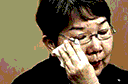“海洋石油981”建造記
通過設計和建造上的嚴格要求,即便是三五千噸的船隻正面撞擊“海洋石油981”,也很難使其發生傾覆等狀況
三年多前“海洋石油981”交付時,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它還只是國家重大裝備制造領域中不太引人注目的一個。
包括這座龐大設備有點拗口的正式名稱:第六代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聽起來也讓普通人一知半解——總之,它很大,能在很深的海洋中鑽井,也許僅此而已。
如今,“海洋石油981”已像南海礁盤上那些巋然不動的主權碑一樣,成為中國在這片海洋存在的象征。

讓我們把目光暫時從西沙移開,投向位於上海浦東的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海洋石油981”的誕生之地。

自2008年4月28日切割第一塊鋼板,到2011年11月30日進行海上移交,大約1000天的 “海洋石油981”建造、調試過程,凝聚了中國人對於海洋的夢想、理解,還有與海洋有關的智慧與技術。

當然,不只是這1000天的努力。向前,人們至少可以追溯到2002年開始孕育的跟蹤項目,乃至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對於此類平台的第一次重大嘗試。

由此向后展望,那些具有更遠大抱負的建造者,正急於彌補“海洋石油981”的一些缺憾,實現未盡的期望。

為海洋權益奠基
時間回到2002年春天,也就是“海洋石油981”正式動工6年之前、平台交付10年之前。
剛剛到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報到幾個月的上海交大結構力學博士畢業生陳剛,被選中參與一個重大項目:“新型多功能半潛式鑽井平台研制”。
它是原國防科工委提出的“十五”高技術船舶科研計劃48個重點項目中的一個。
如今看來,“新型多功能半潛式鑽井平台研制”揭開了中國進軍深水開發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02年,中國新增石油產量的85%來自海洋。
只是當時,大多數人還未關注到它打開的全新世界。
由於國際油價低迷和其他復雜因素,此前20年中國的先進深水海洋鑽井平台一直處於空白狀態,這也是當時整個中國海洋工程低迷狀況的一個縮影。
雖然擁有廣袤的海疆和豐富的海洋能源,但中國上一次對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的嘗試還要追溯到1983年,當時由上海船廠建造了最大工作水深200米、最大鑽井深度6000米的“勘探三號”。
1974年,日本開始在東海中國海域擅自進行能源勘探。國務院和原地質礦產部啟動“勘探三號”項目,以捍衛中國海洋主權和海洋資源權益。
作為2.5代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的“勘探三號”建造歷時十年,期間經歷各種曲折。“但它還是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這個項目的主持者之一、后任國土資源部海洋辦公室副主任的蕭漢強對《瞭望東方周刊》說,“勘探三號”后來還租借給美國、俄羅斯,在全球各地工作。
至今仍在服役的“勘探三號”很好地完成了國家賦予它的使命:它在東海的工作,奠定了今日中國東海系列海上油氣田的基礎。
其中,“勘探三號”完成的最深井就是位於東海的“天外天一井”,它以5000.3米的深度,長久地保持著中國海底油氣井的最深紀錄。產量最高的則是東海“平湖四井”。
此后約20年間,中國在這個領域的技術水平,由“勘探三號”時的世界前列,一直掉落到國際第三集團。
“歐美是第一集團,掌控了主流海工裝備的基本設計,韓國、新加坡是第二集團,是海工裝備制造的主力軍。”如今已經擔任外高橋造船廠副總工程師的陳剛說,“其實這段時間,國際海工裝備制造也在逐步進行產業轉移,從西方國家轉移到亞洲,韓國的海工裝備建造也正是從80年代中后期逐步得到發展,並在新世紀開始發力快速成長起來的。”
到2002年,陳剛他們和中國船舶及海洋工程設計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學等單位啟動“新型多功能半潛式鑽井平台研制”時,手上幾乎是一片空白。
“開始這個課題主要任務是跟蹤,就是了解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設計水准是什麼樣,搞深水半潛平台需要攻克哪些關鍵技術,當時還是以第五代平台為主。”陳剛說,作為一種以深水為主的先進鑽井平台類型,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自1962年出現,代際之間主要以平台的工作水深、可變載荷、鑽井能力等為劃分原則。
2002年為研制“新型多功能半潛式鑽井平台”,陳剛隨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的高層領導到新加坡調研。該國是全球最強大的深水鑽井平台制造地。
“我們在船塢裡看到了一座平台,是第五代。當時看到它的那種心情,就是完全沒有想到我們也會在不久的將來能建造一個,因為當時感覺差距太大了。”陳剛說。
就在2001年,被稱為中國海洋地質之父的中科院院士劉光鼎上書中央,提出“油氣二次創業”的建議。
除了採取新的能源勘查理論,這份報告揭示了中國之前油氣勘探與產出之間的巨大差異,也警示中國將面臨更嚴重的能源挑戰。
此后,一系列能源勘探、開發的課題、項目立項。
“從‘十五’末期開始,國家對海洋能源開發投入加大。接下來的‘十一五’期間,國防科工委、國家科技部‘863’計劃再次投入經費,以我國南海油田的實質性開發項目為依托工程,對深遠海油、氣開發裝備的關鍵技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工信部高技術船舶科研計劃海洋工程裝備專用系統和設備專家組成員肖文生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用一萬張片子“體檢”
2006年夏天,距“海洋石油981”正式動工兩年前。
高橋造船廠30萬噸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船建造現場,當時擔任外高橋造船廠海洋工程部副部長的陳剛遇到了一位低調的訪客。
對方來自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工程建設部,后來擔任“海洋石油981”的項目總經理。而陳剛本人,則成為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海洋石油981”項目的負責人。
“我們聊了一會兒,就談到了中海油決定要建造這樣一個裝備。”他回憶說,這是他第一次知道中國決定建造第六代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對方就是到外高橋造船廠來勘查船塢的。 對於這個消息,陳剛難掩興奮,他連忙向船廠領導作了匯報。雖然此前幾年都在進行相關積累,但這個計劃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有些意外。
其實在2006年7月,國家科技部社發司曾在北京組織召開了“十一五”863計劃“南海深水油氣勘探開發關鍵技術及裝備”重大項目的實施方案論証會。
當時,由劉光鼎等9位院士,會同國土資源部、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船重工集團等單位,對這一重大項目的實施方案進行了咨詢論証。
作為其間一系列重大科研項目的代表,“南海深水油氣勘探開發關鍵技術及裝備”的實施,被認為對於滿足中國深水海洋油氣資源勘探開發的重大需求、使中國深海油氣勘探開發技術實現跨越式發展,意義重大。
院士們的意見是“盡快啟動”。這個重大項目的2.43億元投入中,一部分就流向了“海洋石油981”的關鍵設備和技術。
而此前,原國防科工委、發改委、科技部等已有若干投入。
“我們60%多的油氣依靠進口,如果再不重視海洋,一旦有突發情況,路上的汽車都得停。”劉光鼎院士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一直參與“中國第一船廠”競爭的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自上世紀90年代末建立伊始,就確定了船舶與海洋工程並舉的發展之路。2003年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交付的成立以來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海洋工程項目——海上浮式生產儲油船,即通常所說的FPSO。
2002年至2004年,在陳剛於外高橋造船廠工作的前3年間,外高橋造船廠就交付了兩個代表性的海洋工程裝備:15萬噸、16.2萬噸的“海洋石油111”和“海洋石油113”兩艘FPSO。而在“海洋石油981”之前,陳剛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2007年交付的30萬噸FPSO“海洋石油117”。
除了噸位更大,對於陳剛和他的團隊來說,最大不同其實是整個設計建造流程中的精細和嚴謹。
這艘FPSO由美國康菲公司訂造,用於這家公司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聯合開發的海上油氣田項目。
“前兩個項目做完,我們團隊覺得至少在FPSO這方面沒什麼太大的技術難度了。”陳剛回憶說,但美國石油公司對於海洋工程裝備設計建造的嚴苛要求,對他們來說具有“顛覆性”。
“很多文件從來沒見過,規范和標准無比詳細,比如美國公司要求對全船每一個設備的維護和維修都需要作吊運分析,對所有的關鍵系統都在基本設計和詳細設計上作風險評估。”陳剛說,另一方面,“咱們的人員大多是設計船舶出身,很多設計邏輯和思維都是從船舶設計移植過來的,不適應國際化海洋工程項目對設計方案的安全性、操作便利性等方面的高要求。”
其實,對於以建造散貨船著名的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來說,發展海洋工程裝備不僅是兩條生產線這樣簡單,而是造船文化和海工文化的沖突與磨合。
前者側重於結果導向,按規范設計、採購,按圖施工,檢驗出結果﹔后者則出於對高投入、高風險等因素的考慮,更側重於過程導向,按程序做事,按程序出結果,所有的過程、環節和結果都必須可追溯。
至於建造過程與工藝,海洋工程帶來的是完全不屬於同一級別的挑戰。
“散貨船的結構、鋼板佔空船總重的60%,設備、管線、電纜等佔40%。海洋工程裝備相反,也就是說設備、系統更多、更復雜,它的系統集成工作量是散貨船的5倍以上,包括設備和系統的安裝、機械電氣完工、預調試和調試等等。”陳剛舉的一個例子是,一般轎車上有二三十個傳感器,散貨船有五六百個,“海洋石油981”上超過一萬個。
在焊接完成后,一艘十幾噸的散貨船要進行無損探傷——也就是用類似對人體拍CT的方式查看焊接縫表層和內部是否存在缺陷——需要拍三五百張片子,而一般的海洋工程裝備是照5000張左右。
“海洋石油981”拍的片子超過一萬張。
2006年8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就第六代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發出投標意向征詢函,正式確認了這個項目的存在。
2007年6月,外高橋造船廠提交標書。
2007年10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正式與外高橋造船廠簽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出席簽約儀式。
以上,就是“海洋石油981”啟動建造之前的故事。
焊接長度240公裡
2008年4月28日,位於浦東北端的外高橋造船廠,數控等離子切割機切割了第一片材料,標志著“海洋石油981”正式開工。
建造“海洋石油981”的材料中有大量高強度鋼,因為堅固和安全是對這個巨大裝置的第一要求。
“海洋石油981”總設計師、中國船舶及海洋工程設計研究院海洋工程部副主任沈志平告訴《瞭望東方周刊》,“海洋石油981”的基本要求,就是適應南海的海況。
比如,以百年一遇的風浪作為設計基礎,然后又用200年一遇的風浪進行了模擬檢驗,這相當於遭遇17級台風。
最終,在上海交大的海洋工程重點實驗室對幾十種海況進行了模擬實驗,此外計算機還對1000多種海況作了模擬運算。
另一個要點是:“海洋石油981”有復雜的錨泊系統,也就是用船錨進行停泊。它有12個15噸重的船錨,每個都可以產生800多噸的抓力。
船錨鏈每根長1750米、重約280多噸,其中還加入了以高強度尼龍繩為主的合成纖維索,從而吸收平台移動產生的能量。
在需要時候,這個系統可以每分鐘156米的速度將船錨快速拋射出去,它自己也帶有傳感器,隨時探知自己承受的壓力。
在后來的調試過程中,“海洋石油981”兩次遭遇風力超過15級的台風襲擊,都沒有發生移動。
此外,由於南海海域較大,返回陸地補給困難,“海洋石油981”要求有世界最大的9000噸可變載荷。而這后來又給它的建造帶來了極大的難題。
“海洋石油981’未來將工作於環境條件惡劣的南海,對建造質量的要求幾近苛刻,針對焊接要求高的特點,我們組織了超過2000人的焊工考試。”陳剛說,最好的焊工才被揀選,參與建造“海洋石油981”。
當時負責現場建造的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海洋工程部副部長張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由於大量使用了高強度鋼,給焊接帶來了巨大挑戰:對除鏽、濕度、溫度都有很高的要求,“濕了容易產生氣孔。因為要比較高的焊前溫度,就用電熱夾板一樣的裝置進行預熱,焊接完還要作保溫處理。”
許多零部件的高強度鋼都是從國外進口,“一塊板子返工兩次,就廢掉了。”他說,所有位置的焊接都採用可以追溯的實名制,在探傷檢查時如果發現問題,“直接淘汰責任人。”
整個“海洋石油981”的焊接長度是240公裡,其中包括30公裡平面焊接、210公裡直角焊接。
這個距離,大約是從北京到天津再返回。“由於焊接時要往復焊,焊槍走過的實際距離要遠遠超過這個長度。”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海洋工程部副部長曹志兵說。
對堅固度的苛刻要求,使建造面臨的挑戰幾乎無處不在。比如,通常安裝室內防火門要在鋼板上開方形孔,然而,由於大量採用強度超高、柔性不足的20毫米以上高強度鋼,如果打方孔,四個角會因受力過大而開裂。
經過計算,隻有在四個角上開一定弧度的圓角,才能夠保証鋼板的堅固,但這樣又和防火門形狀沖突。
最終,“海洋石油981”上的防火門都是在圓角的門框上又上下左右各補了鋼板,從而達到安裝要求。
由於需要其他船隻靠近補給等原因,“海洋石油981”也對可能發生的碰撞和摩擦有所考慮。
沈志平和陳剛都告訴本刊記者,通過設計和建造上的嚴格要求,即便是三五千噸的船隻正面撞擊“海洋石油981”,也很難使其發生傾覆等狀況。
最精確的“拼積木”
2009年4月20日,第358天,在外高橋造船廠一號船塢舉行鋪底儀式,“海洋石油981”開始吊裝。
對於“海洋石油981”來說,總體建造過程就像拼積木:首先將其分解成為200多個100多噸的分段進行建造﹔完成后運輸至外高橋一號船塢的組裝平台,再組合成為幾百噸重的總段﹔最后通過1000噸級的龍門起重機吊裝在一起。
這個過程的名稱像個音樂術語——“節拍式總段連續搭載法”,也就是不同部分按照不同的規律進行拼裝。
比如浮箱一共吊裝了20次,間隔大約10天﹔浮箱上的立柱吊裝12次,間隔20天﹔到最后甲板作業平台,則是每3天左右吊裝一個部件。
“吊裝完成一部分后,立刻把大型設備也吊進去安裝,然后再吊裝上邊的總段。比如四個立柱裡都分為幾層,裝有不同的設備。”張偉說,所以“節拍”要拿捏精准。
吊裝84米高、1000噸重的井架,是整個過程中最具挑戰性的環節之一:浮吊裝船要把分成幾節的井架一段一段對應吊裝好,“上下兩個部分就有六個安裝點,要分毫不差地吊在一起。兩個部分都是在海上浮動的,處於動態之中。”陳剛回憶說。
最終這個環節用時500分鐘,效率每小時96噸﹔吊裝效率最高的是浮箱,每小時138噸。
如果從建造工藝上說,最大的挑戰也許是主甲板。
這是一個比標准足球場還大的平台,它面臨的問題是:如果在制造時處於完全水平狀態,一旦安裝到立柱上,中間部分受重力等原因就會下墜,成為一個中間下凹的弧面。
研究了兩個月,最終的解決辦法是:先用計算機精確模擬吊裝到立柱上后、每增加一個建筑所受的力。 根據這些數據,在建造時使甲板有一個上凸的弧面。等吊裝完畢,疊加上井架、生活樓等大約2000噸的建筑、裝備,乃至以后搭載的裝備,凸起正好受力壓平。
如此巨大的甲板,是為了滿足創紀錄的可變載荷:9000噸。
陳剛說,可變載荷大,不僅可以使 “海洋石油981”攜帶更多的柴油和生活補給,增加平台的自持能力,而且可以在主甲板面堆放更多的鑽井工具和設備,更高效地完成勘探任務。
“海洋石油981”可以在水深3000米的地方作業,最深可達一萬米。
與復雜的工藝相比,陳剛覺得,在“海洋石油981”的建造過程中,更多遭遇人的挑戰。
整個建造過程,使用了600萬個工時,也就是600萬人同時工作一小時的工作量。在2009年建造高峰期,平均每天有1200人在現場施工,最高時達到1500人。
“說實話,應該是與近20年的教育有關,培養技能工人的體系基本沒有了。現在找到熟練的機電技能工人很難,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們的發展。”陳剛說。
外高橋造船廠在2005年就達到了年產800萬噸的數量級,負責這些船舶調試的是一個140多人的團隊。
而在“海洋石油981”最后的調試過程中,這一個項目就要上100人。
張偉說,在“海洋石油981”項目中進行高強度鋼焊接的工人,月收入略超1萬元,“成熟的技術工人,過去幾年國內還是很缺乏的。這些年隨著海工裝備的發展,我們自己培養,由老師傅帶著,給他們燒焊,讓他們學習。”
他說,從技校畢業的新手到可以上台面對高強度鋼,需要練習過成百上千塊鋼板。
“海洋裝備的影響太大了。”曾在1958年組建中國第一個海洋物探隊的劉光鼎說,在向西方學習先進技術的同時,重視本國基礎工業的發展,更要注重培養基礎工業人才,“很多高端設備都是手工制造的,我們需要有高端的技術工人。”
17級台風中穩定如一
2010年2月26日,第670天,“海洋石油981”出塢。
離開船塢是一個極其精細的作業過程:由於體形過於龐大,它與船塢的距離,幾乎是外高橋一號船塢生產過的產品中最小的。
在垂直方向上,由於重量過大,它在最高潮位時距船塢底,隻有0.7米。
除了以每分鐘10米以下的速度小心翼翼地移動,在“海洋石油981”出塢時,還要在船塢兩岸派專人觀察它與船塢壁之間的距離,一旦出現問題就立刻把隔斷物塞進去,防止直接摩擦。
為這次出塢,上海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先后專門召開了多次內部論証會,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也召集了國內專家對出塢作業進行了專題審查,包括保險公司、海上拖航、海上安裝等多領域的專家,對出塢作業提出了多項風險防控措施。
2011年夏天,已經離開船塢一年多的“海洋石油981”,進入最后一個關鍵建造環節:在海面安裝8個大馬力推進器。這也是它在南海風浪中保持穩定的最主要依靠。
除了錨泊,“海洋石油981”擁有被稱為“DP3”的動力定位系統——由GPS衛星定位、調整系統和可以360度旋轉的推進器組成。
即使遭遇17級台風,計算機隨時根據定位,調整推進器的方向和馬力,最終使“海洋石油981”穩定於海面一個點。
推進器高3米多,無法在外高橋造船有限公司的碼頭安裝,必須拖航到舟山附近30米深的海域才能完成安裝作業。
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在海上進行深水半潛式鑽井平台的推進器水下安裝作業。
先由浮吊船將推進器吊入水下21.5米處,然后潛水員將推進器上的牽引鋼絲繩拉到浮箱下的提升纜繩上。這樣再用浮箱上的機器通過提升纜繩將推進器拉近,最終對位進去浮箱下的開口。
陳剛說,在東海的風浪中,這項工作一度因為推進器和開口尺寸問題停滯了兩天。
他承認,在歷時3年多的建造過程中,“海洋石油981”遭遇了諸多意料之外的挑戰和困難,“但是我們年輕的海工團隊成功借鑒了從‘海洋石油117’中學習來的先進國際海洋工程項目的管理經驗和設計經驗,平穩有序地推進了‘海洋石油981’平台的設計、建造、調試和海上安裝、聯合調試。”
盡管這一團隊有60%的人員是2006年至2009年才離開學校的新人,每個崗位的平均年齡較世界領先的韓國現代、三星船廠都有10歲左右的差距,但他們是真正和“海洋石油981”一起成長的人。
2012年9月,“南海深水油氣勘探開發關鍵技術及裝備”驗收,它的成果集中在深水油氣資源勘探、鑽完井、海洋工程和安全保障三個方面,“海洋石油981”名列首位。
至此,中國人獲得了在3000米深水進行油氣勘探開發的技術能力,以及4000米深水海洋工程試驗的能力。 在此基礎上,“十二五”期間“863計劃”在海洋技術領域已啟動“深水油氣勘探開發關鍵技術及裝備”重大項目。
“以期為維護我國海洋權益,推動我國油氣工業走向深水和海外提供強有力的技術和裝備支撐。”劉光鼎院士在這次驗收會上提出。
“深水油氣勘探開發與航空航天工業,並稱為21世紀兩大尖端高科技行業。深水鑽井平台和裝備是流動的國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象征,可以以開發行為介入資源保護,作為中國造船的主力軍,我們責無旁貸,時刻准備迎接新的挑戰。”陳剛說,所有的努力就是為了一個結果:提升中國在海洋開發中的話語權。
“海洋石油981”技術帖
空調通風
為滿足衛生要求,“海洋石油981”內每人每小時的新鮮空氣量不小於30立方米。送風換氣次數最多的是洗衣間、烘干間,每小時33次﹔最少的是配電板間,隻有1次。
犧牲陽極防腐
為了防止風浪以及海洋生物、細菌對鑽井平台的腐蝕,使用犧牲陽極的陰極保護辦法——以船體作為陰極,表面附加其他金屬作為陽極,通電后使陽極吸收導致腐蝕的電子等快速氧化。
防火區域
國際海事組織等對鑽井平台的不同區域劃定了不同級別的防火要求。整個平台有超過800個火災探頭以及200多個氣體探頭。火災探測系統使用了“表決邏輯”系統,在一塊安裝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探頭的區域內,當兩個或兩個以上探頭報警時,系統才確認並激活消防動作。
集裝箱加熱
“海洋石油981”的很多部分使用了特殊的玻璃鱗片涂裝。這種涂料物質要求環境溫度必須高於10攝氏度。“海洋石油981”離開船塢准備進行這一環節工作時,正是2011年2月,溫度無法保証。於是在現場放置集裝箱並加熱,使涂料物質在其中保持足夠溫度,即刻涂裝。
鋪設管纜
“海洋石油981”中安裝了7萬米多芯管,為了防止受到焊接損壞,安放多芯管是在焊接基本技術之后。最關鍵的是,整個過程都由人力完成,這使得它必須成為一項極其有序的工作:每天拉放多少、位置、順序以及安排的人員,都需要詳細計劃,否則就會出現交叉和沖突。
每根管子兩端都要標識好接駁的閥門號,並用塑料膠帶包好﹔安放過程中嚴格禁止轉彎和碰撞硬物,防止多芯管破裂變形。
安裝結束后,要用氮氣自一端吹入,達到清潔多芯管內部的作用。這個過程要連續而有技巧,使雜物能夠一步步被吹送至另一端口,然后立刻封死。
包括多芯管、電纜等在內,整個“海洋石油981”上有3.5萬根各式管線,甚至要160人同時安放一根電纜。
天車補償
“海洋石油981”在海上工作時,由於海浪等因素影響而上下運動,從而使鑽井杆也隨之升降,影響鑽進。嚴重時,鑽頭可能脫離井底,無法工作。“海洋石油981”採用了天車補償裝置,當船體隨海浪下沉時,計算機操縱氣缸膨脹推動天車向上運動,從而保持鑽杆在垂直方向處於穩定狀態。當船體隨海浪上升時,同樣通過計算機操縱天車向下運動。
不為人知的海洋衛士
1974年6月,它在黃海開鑽,成為中國第一次在外海進行海洋鑽探年
78歲的蕭漢強,原地質礦產部南沙勘察辦公室主任、國土資源部海洋辦副主任,看到“海洋石油981”的消息總會心跳加速。
20年前,他曾向國務院提出在南沙勘探打井。如今,在強大的海洋裝備支持下,這個願望終於開始實現。
回顧並不漫長的中國海洋油氣開發歷史,一系列幾乎未被國人知曉的裝備,曾經奠定了中國人維護海洋權益的基礎。
如今,以更堅定的高層決心為后盾,海洋工程裝備正在為維護中國的海洋權益貢獻更多力量。
第一次探入外海海底
時間回到1977年底,“十年浩劫”接近尾聲。原地質礦產部聯合原石油工業部等,打算組織一次南沙勘查。
報告一度被批准,海洋調查船、測量船以及測量儀器准備齊全,正要出發,一封上級信件疾馳而至。
雖然已過去30多年,蕭漢強仍然清晰記得這封信的內容:南沙即使有資源,我們也開採不了,建議不要去了。
此次勘查隨即取消。
有關領導對裝備缺乏信心,畢竟那是中國海洋工程裝備剛剛起步的歲月。
新中國的海洋油氣資源勘查長期是一張白紙,僅在1958年開展過一次海上地震試驗。
當時以北京地質學院地球物理教研室教師劉光鼎為領隊,中國科學院海洋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質部物探局、石油工業部及其石油科學研究所、北京地質學院等青年科學家,組成中國第一支海上地震隊,借鑒陸地地球物理勘探方法,將炸藥包投向大海,第一次記錄下人工激發的地震波穿過海水、透過海底表層的反射信號,邁出了中國認識海洋深處的第一步。
到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公布了在中國東海的一系列勘查成果。高層領導由此意識到開發海洋工程裝備的重要性。國務院最終決定改裝、建造和進口鑽井船各一條。
劉光鼎等人受命在上海參與成立“627工程”籌備組,即后來的上海海洋地質調查局,之后還成立了第三海洋地質調查大隊,作為專業海上鑽井隊伍。
劉光鼎本人則任上海海洋地質調查局副總工程師。
這位地球物理學家、海洋能源開發專家、中科院院士向本刊記者回憶說,早期的海洋勘探、勘查十分困難。由於美國和蘇聯都對中國封鎖,無法從國外購買先進儀器,隻能自己想辦法,比如把陸地地震儀改裝為海洋用設備,“今天看水平確實很低,但總是一個創新、一個開始。” 最終,中國人決定用交通部提供的兩條3000噸級舊貨輪拼裝成一條鑽探船。
“就是將兩條船平行,焊接鋼板固定后,在中間架上一台陸地鑽機,建成后叫‘勘探一號’。”蕭漢強說,
1974年“勘探一號”正式服役,雖然隻能在水深90米以內的海域工作,6年中還是在南黃海區域鑽出7口油井。
特別是1974年6月,它在黃海開鑽,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外海進行海洋鑽探。
但是受到建造和設計水平的限制,該船平衡能力較差,無法承受稍大的風浪。加上服役不久船體就嚴重變形,以及受到腐蝕等問題的干擾,“勘探一號”很快就退役報廢了。
用幾千萬美元認識南海
在這段時間,原國家計委也打算從國外引進海上鑽井平台,經過調研國際市場后,得知每個平台價格約為四五千萬美元。
通過華僑介紹,一個新加坡船廠老板答應幫助中國制造鑽井平台,“他也沒有技術,雇美國人幫他設計,還從世界市場上買了鑽機。”
這個產品就是后來的“勘探二號”。
幾千萬美元的數額在當時的中國幾乎難以想象,“當時的廣交會上,一個用玉石雕刻的雞蛋那麼大的鴛鴦,才賣1美元。”蕭漢強說,而當時糧食的價格隻有七八分錢一斤,雞蛋大約4分錢一個。
相對於拼裝的“勘探一號”,由美國技術制造出來的“勘探二號”顯然更加先進。這是一座自升式鑽井裝置,雖然作業水深仍然不超過100米,但已經可以在東海區域較大風浪的條件下作業,於1977年春末到達珠江口萬山錨地開始服役。 此后兩年,“勘探二號”一直在南海珠江口盆地作業,共鑽井7口,並打出了珠江口盆地第一口工業油氣井“珠海五井”。
在珠江口盆地的鑽探,為后來中國與國外合作開發這一區域的談判提供了基礎和條件。
1980年之后,“勘探二號”自南海北上,在東海開鑽“龍井一井”。
當時在鑽進過程中發現多個地層含有油氣,但即將突破3500米時發生故障不得不結束。這也是中國在東海完成的第一口井,至今仍在工作。
1981年夏天,“勘探二號”完成井深4200多米的“龍井二井”,1983年完成井深4600多米的“平湖一井”,這是中國在東海油氣勘探的第一個重大突破,奠定了平湖油氣田的基礎。它一直在東海服役,直到1992年退役。
壯志未酬的“勘探四號”
“如果我們自己有更好的鑽探船,就可以更准確地評價海裡的油氣田。”蕭漢強說,有了“勘探一號”和“勘探二號”的經驗,中國決定自己建造鑽井平台,也就是2.5代的半潛式鑽井平台“勘探三號”。
經歷約10年的努力后,該平台終於在1984年交付使用。在吸取“勘探一號”以及“勘探二號”的經驗教訓后,“勘探三號”當時達到國際上同類型半潛式鑽井平台的水平,並拿到了中國船級社和美國船級社的入級証書。
在蕭漢強眼裡,造價1.5億元人民幣的“勘探三號”,不僅承擔了到東海進一步勘探的任務,還為去南海勘探做好了准備。
為了進一步勘探開發海洋油氣資源,上世紀90年代,原地質礦產部向國務院報告,希望購買更先進的鑽井平台。
這份報告被批准,並獲得超過10億元人民幣的經費。隨后,上海海洋地質調查局向美國西方海洋有限公司購買了后被命名為“勘探四號”的半潛式鑽井平台。
“勘探四號”由新加坡一家造船廠建造,自帶助推器,工作水深達到600米。
據蕭漢強介紹,購買“勘探四號”后,他們在南沙區域選好了井位,但一直沒有得到開鑽的批准。
“從1995年往后我們變換了十幾個井位,但一直沒有獲得批准。”
“勘探四號”於是一直停留在挪威海域,再后來劃歸中國石化集團用於出租經營。
如果從原地質礦產部在1970年開始籌備海上鑽探算起,到2000年,其間30年的中國海上鑽探,被業界稱為“慘淡經營、艱苦創業”。
雖然鑽井平台一度有所突破,但其他配套裝備、船隻幾乎一片空白。
劉光鼎回憶說,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有一家美國企業將船開到珠江口推銷儀器,中國的科研人員才發現差距巨大。
他曾到法國購買了一條正在維修的地震勘探船,也就是“奮斗七號”,“主要是看中了他們船上的設備儀器,包括地震檢測儀器,包括炸藥等,都拿來研究。”這條船買來后再去曾經勘查過的海域進行測量,數據差異巨大。
劉光鼎說,包括意識在內,很多基礎的問題不解決,不僅影響油氣勘探,甚至也會影響國防。
中國油氣的出路在二次創業
2001年8月17日,劉光鼎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份關於中國油氣資源第二次創業的報告。 這份報告的背景是:1993年成為石油進口國后,中國的石油消費年均遞增6.7%,而同期國內石油生產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6%。
就在1993年,中國進口石油3000萬噸,其后能源成為國家經濟建設持續發展的瓶頸。
而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中國曾完成了油氣資源的第一次創業,使原油年產量達1.67億噸,天然氣產量達241億立方米,分別位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十五位。
另一方面,雖然上世紀末預測的石油、天然氣資源量都很大,其中石油940億噸,卻隻探明了22%﹔天然氣38萬億立方米,僅找到了7%。中國油氣的出路在二次創業。
劉光鼎認為,除了陸上油氣資源可以採用新理論,海洋將成為中國能源二次創業的基礎。
此報告發出十天后,就得到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的批示。
此后,一系列圍繞深海開發的課題、項目在多個部委立項,包括為南海勘探定制的“海洋石油981”。 不過,在蕭漢強看來,之所以造成目前周邊國家掠奪南海資源、侵佔南海島嶼、“小國欺負大國”的尷尬局面,原因首先仍是中國人海洋意識的淡薄,“沒有充分認識到海洋對國家安全、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
直接后果就是忽視海洋權益,當然也就忽視了海洋裝備的發展,“包括當時一些系統內的干部,也認為我們國家根本顧不上這些事情。”蕭漢強說。
劉光鼎耿耿於懷的則是,“文革”結束后,他曾給上級寫信,認為雖然簡陋、落后,但畢竟有了船和基本設備,可以到南沙、曾母暗沙去勘察,結果沒有得到支持。
“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能挺近南海,進軍東海,並堅持下來,今天肯定是另一番局面。”蕭漢強說,“周邊國家已經在南海開採了12億噸以上的油氣,那裡有我們的資源。”
幾十年后的今天,看到“海洋石油981”終於“釘”在西沙,蕭漢強很欣慰。他說,這是幾代人的夢想。
(本文參考了《海上鑽探三十年》(《探礦工程》1999)等公開資料)
(原標題:為南海而生——你所不知道的“海洋石油981”)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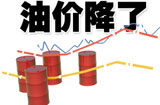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