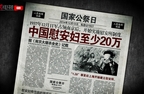這是一項要求極高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校時,就經歷了非常嚴格的選拔。
“專業成績優秀是最起碼的。”調度處處長袁運棟說,“心智要穩定,既要膽大,也要心細。”
在這位“老調度”看來,盡管如今工具先進多了,環境舒適多了,但石油人四海為家的工作性質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而成為一名優秀的油氣管道調度,就像管道本身一樣,沒有捷徑可走。
在真正上崗之前,這些年輕人經歷了一系列的“武裝”和“實戰演習”。他們被送往上海、沈陽、北京的調控中心接受有針對性的培訓,在不少國內管道段落進行實習,培訓外語,還被送到加拿大參加“強化訓練營”。
按照這一行通常的做法,調度崗位一般會由經驗豐富的“老同志”擔任。而在這裡,年輕人們必須在兩年內完成通常需要三五年甚至更長時間完成的任務。
“但就因為這樣,我們成長得特別快。”2011年畢業於大連理工大學的王洋龍說。
剛打完籃球,這個小伙子身上還穿著背心短褲,汗水順著臉頰不停地淌。但說起自己的工作,他顯得很鄭重。
“我來之前,就被告知石油人的艱苦,當然也知道調度的要求。”他說,“但我自認為踏實穩重,能夠勝任。”
在曼德勒調控中心,他能夠接觸到國際領先的調控系統,並承擔更為重要的工作。同時,他還必須堅持學習,不放棄研究。
“我非常珍惜這個崗位。”王洋龍說,“因為我能夠參加這麼重大的項目,還做著這麼核心的工作。”
在他看來,和他一同畢業的同學們,也許還沒有獲得這樣的機會。
想到這些,夜班的辛苦和海外的孤寂,似乎就沒有那麼難熬了。到緬甸快3年,他除了想念家鄉大連的魷魚絲,“其他都還好”。
漫漫石油路上年輕的心
當油氣管道穿過國界,回到祖國,另一群年輕人也在沿線為夢想奮斗著。
瑞麗首站,正在施工的場站工地上,常常看得到清秀白淨的姑娘。她們不化妝,也沒法穿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統一制服、工程靴、安全帽是標准配置。
場站總工石鵬遠也是80后。他說,在這個號稱“中國地質博物館”的地方,女員工和男員工一樣,得吃得了苦,忍耐得了孤獨。
而在這條龍脊般堅定綿延的管線最末端,廣西貴港站,年輕的女調度員坐在電腦前,挂著大大的黑眼圈,若無其事地說著值夜班的經歷和場站的規劃。
“對外面的人來說,這一路都是優美風景。但對管道人來說,美好的表面下,是巨大的困難和危險。”一位管道局負責人說起建設這項超級工程的艱難。在巨大的壓力、焦慮和工作強度下,甚至有人倒下,就再也沒站起來。
“我的工作有意義!”張勇激動地說,“緬甸人民和祖國人民都用上了這裡傳回去的天然氣。”那是2013年7月28日,管道開始向國內通氣,這位帶班調度長站在曼德勒調控中心的調控台旁,從監視器中看著南坎的火炬沖天燃起。
2012年,28歲的張勇從西氣東輸二線轉戰到中緬油氣管道項目,從此,他的“戰場”從荒涼的戈壁換成了旱季炎熱、雨季悶濕的緬甸。那時,調控中心籌備組剛剛成立,5個人擠在7平方米的辦公室裡,電力供應很不穩定,每天至少停電20次。斷網更是家常便飯。有一次,他要收集現場監理發送的數據,正趕上網絡不通,手機信號時斷時續,隻能用備用電台呼叫,人工記錄。
這樣的工作效率下,項目依然如期完成。他全年累計休假不足50天,每次回家時,看到兒子陌生的眼神,他心裡全是愧疚。
家人,是有家的年輕人最難以提起的話題。而對於那些還沒成家的年輕人,“成不了家”才是最大的問題。由於常年漂泊在外,石油小伙子很難維系和女朋友的關系。有些姑娘一聽說不能陪在自己身邊,干脆連相處都不願意。
“女生湊在一起聊男生,那麼男生湊在一起……”尹航笑著說。這個1988年出生的小伙子常常和“兄弟連”探討怎麼搞定女朋友。事實上,馬德島上一個女工作人員都沒有,這些男生剛從校園出來,一頭又鑽回了“宿舍生活”。
不過,年輕人多的地方,從來不缺少活力和創造。工作之余,男生會湊在一起打籃球,周末偶爾也會喝上兩口小酒。板房宿舍的牆壁上貼著球星的海報。有人學起了攝影,有人自制健身啞鈴。時不時的,他們還和海那邊的皎漂管理處踢場足球賽。上一次的結果,是“10︰4大勝”。
元宵節和情人節一同到來的那一晚,於飛和同事喝了幾杯酒,往靠近碼頭的宿舍走。在潮音中,他聽到籃球場傳來隱隱約約的吉他聲。
年輕的喉嚨唱著:“親愛的小孩,今天有沒有哭……”
至少那天,於飛沒哭。他心裡清楚地知道,在自己未來的漫漫石油路上,這座小島才僅僅是第一站。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於飛為化名)
| 上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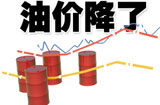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