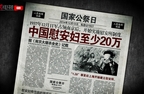政企分开当向纵深推进
对话人物
彭建武 西北工业大学焊接专业学士学位,湖南大学EM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从农村吹起时,政企分开就被提出,并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与核心。三十多年后,政企分开依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讨论的焦点。虽然政企分开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政企分开问题,半月谈记者对话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建武、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管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半月谈记者: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彭建武:在我看来,国企改革的关键不在哪种资本占主导地位,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但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即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政府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能时,只能当老板、当股东,不能当婆婆。可以说,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质量,决定着国企改革的成效。
半月谈记者:结合当前国企改革实际,推进政企分开应在哪些地方使劲?
彭建武:从大的维度看,政企分开涵盖两方面——形式上和内容上。形式上,国企要把自己承担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移交出去,企业只负责搞好日常经营工作。内容上,政府应更多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协调和宏观指导,而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事务与运营。
政企分开的内容还包括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分离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要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同时,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必须分开,同一政府机构不能既承担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又承担行政职能。
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可实际情况如何?不少国企的董事会、监事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企关系理不顺,政府仍可通过各种手段管控企业。因此,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彻底放权,让企业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政府放权就是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项目审查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等。
梁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有两方面:
一是坚决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不管隶属关系如何、行业性质有多特殊,只要是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所控股、参股的国有资产,都必须接受国资委的集中统一监管,禁止政府组成部门直接经营企业。
二是限制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图,应通过国有股东的权利表达机制向国企传导,不得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干预国企自主经营行为。国资委通过有效的考核机制,引导国企服从国家大局,履行社会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与国企的“分开”,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而不是国有资产与国家及全体人民分开,亦即不能搞全盘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同时,在去行政化、与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国企国资拥有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所有者缺位”。
李锦:我们的国资监管改革要善于用好两把刀:一把刀要切开国资委与企业的联系,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经营公司;另一把刀要切开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联系,根据国企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仿照公务员管理,总经理则完全从市场聘任。用好这两把刀,不取决于办法,而取决于决心。现行的国企领导人既享有行政级别的党政干部待遇,又能拿到市场化的高薪酬,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结束了。
半月谈记者:改革是一种利益的再调整,同时也会伴生阵痛,包括企业本身、企业员工都会经历“阵痛期”,如何看待?
彭建武:目前,我国政企分开不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层面虽有宏观指导政策,但具体操作政策却没有出台。一些国企承担的政府职能虽已移交,但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却未移交到位。比如,我们公司离退休人员的人事管理和企业补贴以及离休人员的医疗费用仍需企业承担,每年花费约4000万元。就连生产区外的社区(原来属于厂区范围)园林绿化等工作也得企业承担,每年支出700余万元。
政企分开后,地方政府要承担一笔财政负担,而目前很多地方财政吃紧。作为企业,在向政府移交社会职能时也要交一笔经费给地方。这笔钱怎么支付?目前国家也没有出台具体规定。建议企业在转让社会职能时,支出的经费能够被列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政企分开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政企分开的另一个难点是移交职能时利益调整难度大。比如,企业向政府移交医院和学校时,职工非常愿意,因为移交地方后,是按照普通事业单位给予编制,退休待遇要好于企业。然而,厂区园林绿化和离退休管理等职工则不愿意。因为对这部分人,地方政府没有编制安排,只能聘用,待遇要比企业差很多。
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出现“阵痛”是正常的。当年为了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开设厂办集体企业。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这类企业与主办企业没有人事关系、股权关系、资产关系,其经营大多是配套主办企业,经营好坏与主办企业没有关联。近年来,这些企业很多身处困境。我们公司旗下一个厂办集体企业十多年没有正常运营,职工每月只拿100元的生活费,生活非常艰难;而且大部分职工都在50岁左右,自我谋生的能力有限。
按照相关文件,这些企业的改革成本是由国家财政、主办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2008年就开始了改革试点工作,但目前并未全面铺开。一大原因就是缺乏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难以确定安置人员的安置项目和标准。只要有政策,哪怕是借款,我都愿意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总是心头的痛。
梁军:国企国资市场主体地位的强化,不能以牺牲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代价。所有的改革努力,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措施,看似完美无缺,满足了市场化的所有预期,但是最终指向了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比重中越来越少,或产生了“一放就乱”的倾向,或最终仍旧是国企自身独享改革发展的红利,那再怎么改,也是失败的。(记者 阳建 陈春园 林超)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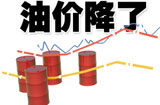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