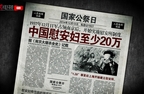在改革中完善农地流转
对话人物
夏祖相 重庆市农委主任。重庆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近年来,积极探索创新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先后在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推进,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外转移,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趋势明显,迫切需要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途径,创造农业发展的新活力。不过农地流转也存在诸多风险和难点,半月谈记者就其中的几个热点话题,与重庆市农委主任夏祖相进行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规模农业、效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流转,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也首先需要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利用。那么在目前基层土地流转实践中,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之变,到底能为农业发展带来什么?
夏祖相:在重庆这样的西部农区,我们发现,通过土地流转,一方面盘活了农地资源,改善了农村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较低的情况,使土地供需双方实现了较好对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相较于过去单纯依靠种养业和打工收入,现在农民也有了像土地租金、分红、务农工资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据初步测算,目前重庆全市每亩土地平均流转收益达到500元,土地流转收益总额可以达到50亿元。
半月谈记者:根据现行土地承包法,到2028年,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农村承包地二轮承包将到期。我们曾到全国10多个省份调研,发现不少地方干部、农业大户和专家学者对二轮承包经营期限到期后政策走向有各不相同的看法,有农民因此担心失去耕地不愿进行流转、也有大户担心政策变化不敢持续投入。如何从制度建设上,消除土地流转的这些顾虑?
夏祖相:农村土地流转必须放在中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两个维度中考量。在城镇化过程中,对选择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应进一步从法律层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具体规定,通过确权稳固农民的承包权;对于今后转户进城的农民而言,则要保障其土地财产权,探索完善的“人地分离”机制。
从重庆的情况来看,自2010年开始实施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来,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有384万农民自愿转户。不少转户农民的土地以代耕、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没有出现大面积撂荒,农业生产总体平稳。这初步表明,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土地租金收益等方式,可以鼓励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不过要从根本上消除上述顾虑,还必须从法律上明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方式,把农民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其土地的各项权能落实,并加快研究和出台保持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和稳定的具体规定。
半月谈记者:伴随着土地流转加快,规模化的新型经营主体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不少人关心,农村承包地抵押担保能否缓解农村金融“缺血”的老大难问题,同时这项改革对农地流转又意味着什么?
夏祖相:首先应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实质上是以一定时期土地经营的农业预期收益去抵押担保。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的试验区,早在2010年,重庆就开始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试点。经过近4年试点,重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改革总体平稳,试点范围已经覆盖全市所有涉农区县,金融机构呆坏账率始终控制在安全水平,农民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种养业、林业、农副产品加工等,满足其产前、产中、产后资金需求。
从重庆实践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主要作用在于:一方面激活了承包地财产权能,带动农民土地财产有效流动,解决贷款缺乏抵押物的问题;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比,额度更大、期限相对较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专业大户、经济能人的资金需求。显然,这项改革对于缓解农村资金缺口大有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农地流转,尤其是提升部分新型经营主体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和积极性。
半月谈记者:我们在重庆农区调研发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主体多不是普通农户,而是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的农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这些新型经营主体贷款积极性更高,对资金需求也更大。但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农民土地,向银行贷款,应该如何防范其中的风险,如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呢?
夏祖相:正如你所看到的,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零星、分散,规模偏小,抵押价值低,这是不少地区推进承包地抵押贷款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在重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中,贷款主体大多不是散户农民,而是规模经营主体。贷款抵押物也主要是土地流转后形成了一定规模效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随着我国农业经营方式不断创新,土地制度所处的宏观背景和微观基础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承包地逐步走向“保障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新阶段,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新型农地制度,有望为进一步解锁农地抵押难题创造制度基础:其一,承包户仍长期拥有土地承包权,保障农民“不失地”;其二,允许土地流转后的经营者将其持有的经营权进行抵押,不影响承包户与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
同时,承包地抵押融资门槛的放开,不仅是在政策设计上放开承包经营权抵押的限制,还应该完善配套机制,建立抵押贷款风险补偿基金、抵押担保、政策性保险等,形成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推动承包经营权抵押融资健康发展。
半月谈记者: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资本借机“圈地”,导致“圈田占地有后患、规模过大有风险、农地改用破底线、挤出农民无处去、套取资金搞运作”等问题,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通过哪些制度设计,能真正使资本下乡服务农业、服务农民?
夏祖相:我们应正确看待城市资本下乡对农业农村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方面资本下乡在整合农业要素、培育农村市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格局等方面具有积极效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资本下乡过程中,有企业“嘴上念着‘农业经’、心里算着‘土地账’”,出现了“非农化”“非粮化”等问题,应该加强引导,趋利避害。
那应该如何规范引导呢?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对资本直接经营农地“定规矩立门槛”,尽快从政策或法律层面因地制宜地对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农地的期限、规模、涉足领域设定明确的标准;对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领域进行明确界定;明确规定社会资本参与土地流转必须先交纳年流转租金一定倍数的资金作为“风险保证金”,防止企业中途退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及对土地进行掠夺性经营。
近年来,重庆在大足、梁平等部分区县,进行了大宗土地流转审查备案和预警制、土地流转风险保证金制等试点,对于规范土地流转行为、促进规模农业健康发展有积极作用。(记者 李松)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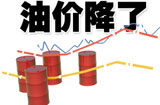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