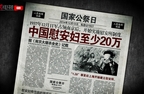教改有风险 不改有危机
对话人物
朱清时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2009年9月,已经退休的朱清时“重出江湖”,被深圳市政府聘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将南方科技大学形容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推动南科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教育公平、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采用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模式,使之向着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奋进。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备受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2012年正式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一块重要的试验田,学校实行的“6+3+1”招生、考试制度颇具借鉴意义。近日,半月谈记者就招考制度改革和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展开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高考改革是教改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这项改革的必要性,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国家要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教育是根本,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很难给国家创造大批创新人才。在这一点上,大家早已形成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教育怎么才能为国家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其实很多人心中有数,教育部门也早就提出来,就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转成功?关键就是高考指挥棒和素质教育不协调,高考对学生、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影响太大,怎么能考上大学,大家就怎么做,所以忽视了素质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甚至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就是高考改革、高考创新。
半月谈记者: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的说法,您怎么看?
朱清时:当前的高考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高考改革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怎么考”的问题,也就是高考指挥棒“指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高考不只注重学生的做题能力、应试能力,也考察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那么高考指挥棒就可以带动并促进素质教育。
南科大在招生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探索这样一条新路,不仅考查学生做题能力,而且考查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包括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等。
半月谈记者:南科大致力于招生、考试改革方面的探索,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进展?
朱清时:2012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南科大试行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学生依然参加高考,但是分数仅占总分的60%,余下的比重,能力测试占30%,平时成绩占10%。能力测试,或者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就是要测试学生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具体说就是批判能力、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注意力等。根据这两年的实践,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对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判。
南科大2012年招了188个学生,2013年招了388个学生,今年我们计划招收600名本科生。我希望通过南科大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验证这套招生、考试制度的可行性,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最终促成全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的变化,让大家知道,要考上大学,不只是会做题,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
半月谈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介绍的“6+3+1”模式中,并没有面试环节,既然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什么不设面试?
朱清时:对,为什么南科大招生不面试?最主要的原因是考生太多,教师太少,面试成本太高,速度太慢,所以现阶段只能用笔试来测试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为了保证面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每个学生需要面试近20分钟,南科大每年有几千名学生报考,这个成本计算起来确实难以承受,不设面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半月谈记者: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过传统体制的束缚?
朱清时:有的,很多现有的规章制度是不利于南科大办学的。比如我们已经招了140多名优秀人才来当教授,90%以上都是国外回来,很多教授每年都需要出国交流或者学习,但是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很严格,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很多持美国绿卡或者拥有美国国籍的教授,报销就很困难。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授出国交流就困难重重。
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建设一些实验基地,又要报批,又要招标,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完这些程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很多教授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开展科研工作。
更尖锐的问题是,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所有教职员工都没有事业编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觉得拿不到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没有安全感。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想给工作人员发事业年金,给他们更多的保障,但这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
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您认为当前教育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清时:教育改革最大困难在于,对改革的具体方案很难形成共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对于一些改革探索,但凡是有看不惯的地方,就会批评、攻击,这种批评往往缺乏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是个人主观倾向的表达,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和失败的风险。
南科大做的事情要经历史去检验,现在看来,这些探索还难以和蔡元培、梅贻琦这些教育大师当年所进行的改革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改革的过程往往都是最艰难的,蔡元培、梅贻琦在任上做出的改革都遭到过很多反对,几十年后才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教育改革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期望所有改革之举当下就能赢得一片喝彩。
半月谈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
朱清时:我想过,而且觉得很有可能会失败,用短短几年时间来做教育改革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弊病根深蒂固,不是几个人就能消除的。我之所以有勇气敢于去做,是期望通过南科大的实践,让全社会都了解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和体制弊病在什么地方,这样今后才可能有人会成功。
如果南科大最终成为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教改的样板,帮助推动产生一批创新型大学,那当然很好。但就算最终改革成功的不是南科大,如果我们能帮别人看清楚中国教改的难点和症结,那也算是我和南科大的欣慰了。(记者 郑天虹 詹奕嘉)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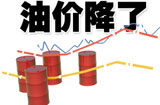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